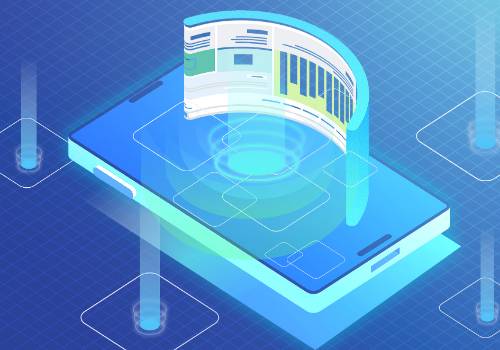撰文|蔡磊
摘编|周琪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对 45 岁的蔡磊来说,人生分为两段。41 岁之前,他事业有成,建立家庭,初为人父。他曾长期担任京东集团副总裁,是中国电子发票的推动者。而在 41 岁这一年,他收到了一纸“渐冻症”的确诊通知书。
“渐冻症”是一种罕见病,全球患病率为 5.2/10 万,平均生存期 2-5 年。数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出这个罕见病的发病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但进展有限。对患者而言,它比癌症更可怕。得了这个病,只能缓慢而不可逆地一步步走向让人失去尊严的死亡。
如果你长期关心蔡磊,会注意到他的身体状态正在肉眼可见地变差。2022 年是他病情进展最显著的一年,年初左臂无法平举,年中发现右臂也抬不起来了,手指也一根根倒下,失去了力量,只能用脚踩装置来操作鼠标。更难的是,伴随喉部肌肉的萎缩,说话开始费劲了,发音慢慢含糊,以前讲一遍就能语音识别,现在总要讲好几遍。吃东西时,普通大小的汤圆变得难以下咽。
但他依旧在和时间赛跑,推进“渐冻症”患者遗体和组织样本捐赠,搭建最大的“渐冻症”病理科研样本库,设立公益基金与慈善信托,对早期科研给予持续资助,推动多条“渐冻症”药物管线的建立,开启直播对“破冰”事业持续支持……用他自己的话说,打光最后一颗子弹。
相信蔡磊的故事与精神会打动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在沉重的疾病与命运前,在面临几乎不可能之时,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以下内容摘自蔡磊所著《相信》,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人生倒计时
从住院第一天起,我就开始了解渐冻症的相关知识。起初是通过网络搜索看一些官网,后来开始查专业文献,把国内外学术期刊网上所有可以找到的关于运动神经元病,包括关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论文,全部下载下来,逐字逐句地读。为了提高读论文的速度,我还找到了专业的医学翻译软件。夫人是药学出身,她一看,软件翻译得很准确。经她验证后,我便开始海量地翻译、阅读,翻译、阅读。
读得越多,越了解这个病,我也越能体会到樊医生(北医三院神经内科主任樊东升教授)说的这个病的残酷之处。
神经退行性疾病一般是指由神经元逐步凋亡或功能受损导致的疾病。像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都是重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只是作用于不同区域的神经元细胞。当中脑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受损或凋亡,经常会导致帕金森病;当颞叶内侧海马神经元细胞死亡,人的记忆会退化,一般表现为阿尔茨海默病;而当运动神经元出现问题,则会导致运动神经元病(最典型的是肌萎缩侧索硬化,俗称“渐冻症”)。
人体的骨骼肌是由运动神经元支配的,当神经元凋亡,肌肉失去了支配,就会逐渐萎缩,以及出现腱反射亢进、肌张力增高、肌束颤动等症状。
“肌肉逐渐萎缩” 6 个字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喝水、吃饭、穿衣、上厕所、拿手机、打字、发声……你会眼睁睁看着这些曾经轻而易举的事情变得难如登天,甚至你都没法自己翻身。疾病发展到后期,人的身体会像“融化的蜡烛”一样坍塌下去,无法说话,也无法吞咽,“吃饭”要靠胃管往胃里注入食物,呼吸需要靠机器维持,大小便无法自理,排便的时候需要人工去抠。人会活得毫无尊严可言。
其实“渐冻症”专指肌萎缩侧索硬化,后来民间将其含义逐渐扩展了,也用来描述有类似症状的其他疾病,不过这样是不确的。虽然媒体上时不时会出现“某某渐冻症患者被治好”的消息,但严格来说,目前能治好的都不是肌萎缩侧索硬化。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的平均生存期仅有 2~5 年,就算有人一天 24 小时寸步不离地看护,鲜少有人能活过 10 年。
世界上最极端的例子是霍金,这位全球最著名的渐冻症患者, 21 岁确诊后,医生判断他只能活两年,但他顽强度过了 55 年, 76 岁去世。之所以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一方面得益于他本人乐观向上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渐冻症的分型不同,这也是影响患者生存期的决定性因素。近年研究主要将渐冻症分为数个临床表型,霍金的病型有可能属于一种可以避免呼吸系统受损的疾病类型。几乎大部分渐冻人最后都是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所以如果呼吸系统不受损,患者通常存活率较高。
当然,霍金的奇迹也有赖于顶尖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细致护理。他日常的进食主要依靠护理人员,避免了可能因吞咽肌肉退化导致的脱水或营养不良。对于他,可谓倾国家之力去维持他的生命,最先进的医疗设施、最专业的护理团队,成本高昂到一般人无法想象。
所以,他的案例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例,是所有渐冻人都无法企及的幸运。
对普通患者来说,就算有人全程照顾,想维持住他们的生命也并不容易。渐冻症患者的死因各种各样,有呼吸受阻、被一口痰堵住导致死亡的,有呼吸机突然断电而死亡的,有绝食、自杀的,也有被家人放弃而死亡的。
还有一种情况——走路摔死的,这个死因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普通人走路摔跤的时候,会本能地用手撑地,保护头部,而上肢发病的渐冻症患者,两只胳膊丧失了支撑的力量,只能眼睁睁地让自己的头砸到地面,有时候就这样直接摔死了,即使没摔死,也要缝上十几针。
不管是毫无尊严地活着还是意外凶险地死去,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相比之下,安乐死能够没有痛苦、相对体面地结束这一切,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现在说起来像笑谈,但当时我们四五个差不多年纪的病友,曾认认真真地研究过路线、流程以及如何联系,想要组团去死。直到一个病友联系了瑞士相关机构,被告知一个人的费用大概要 30 万元人民币。
“ 30 万元?算了算了,别再给家里添负担了。”至此大家就没有再讨论过这个话题。
死都这么贵,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老朱从不参加“组团赴死小分队”的讨论,他说他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我死了就死了,但是能多撑两天就多撑两天,能多领几个月工资,媳妇孩子就有饭吃。”
说这话的时候,我俩站在病房的窗户前。楼下一个捡垃圾的流浪汉恰好经过,老朱打住话头,盯着那个身影,眼里全是羡慕。想必我目光的成分跟他并无二致。那个流浪汉能四肢康健地沐浴着阳光,而且,似乎拥有绵延的生命。
而我们,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剩下的日子,
你要怎么过?
人真是一种复杂的动物。我一边研究死,一边海量地查文献、看论文,想要找到活命的机会;一边觉得自己已经接受现实,接受死亡,该工作工作,该开会开会,一边又在夜里辗转反侧,盯着黑漆漆的屋顶发呆。
其实从第一次见樊东升医生的那天开始,我就睡不着觉了。住院后,这种情况变得越发糟糕。
医院晚上 10 点统一熄灯,我习惯性地在手机上继续处理一些事情,仿佛只有在工作、钻研文献时才能暂时忘记自己的病人身份,一旦躺下,潜意识中的绝望和焦虑马上就会奔涌而来。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却感觉闭着眼比睁着眼时看到的东西还多、还杂。耳边细微的嗡嗡声让一切显得不真实,我分不清那个声音来自耳朵还是大脑,是梦境还是现实,只觉得夜晚的安静又将那个声音放大了数倍。迷迷糊糊之间又突然完全清醒,点亮手机,2:06。左臂上的肌肉仍在持续地跳着,像是在用尽全力跟我做最后的告别。想想未来几年里,全身上下的每一处肌肉都会相继丧失功能,直至全部丧失。2 年?3 年?或者老天眷顾,能留给我 5 年?脑子里闪着这些数字,慢慢模糊,不知多久后又瞬间变清晰,一看时间, 3:20。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不,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为什么不能多留给我一些时间,为什么是我……一连串的“为什么”“凭什么”“怎么办”旋转着涌入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我被推搡着一直往前却一直走不出去。等终于看到前方一个亮点,像是隧道出口,一睁眼,时间已经指向 5:00。护士要来抽血了。
有半年的时间,我每天夜里几乎都是这种状态,即便勉强睡着,一晚也要醒四五次。这种状况在病友中极其普遍。绝症患者一般都会伴有心理问题,在海啸般的绝望、恐惧、焦虑面前,人会被瞬间吞噬。不少人会陷入抑郁,所以医生会主动给开一些抗抑郁的药。
我的药也摆在床头柜里。这类药多少都会有些副作用,会让人昏昏欲睡,那样的话日常工作、开车都会受影响。我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一粒都没吃。吃药后昏沉的大脑和睡不着觉困倦的大脑,我宁愿选择后者。既然我明确知道海啸的源头在哪里,那么与其在下游拼命地舀水,不如直接去根源解决问题。
我也同样拒绝吃力如太。目前它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延缓渐冻症,能够从死神手里抢下 2~3 个月存活期的“特效药”。住院第 17 天,医生给我开了一盒,让我赶紧吃起来。
之前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仍多多少少抱有希望,觉得自己可能并非渐冻症。毕竟做了两个多礼拜的检查,医生始终没有写下明确的诊断。而“力如太”的到来则无异于用另一种方式宣判了我的死刑。
如果真的是渐冻症,多活两三个月有意义吗?
躺在床上睡不着,我就戴耳机听李开复的《向死而生》。这是他在战胜淋巴癌之后写的书,与死神擦身而过,让他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在书中,他得出了一个朴素又近乎是真理的结论:健康、亲情和爱要比成功、名利更重要。李开复从中获得了对抗疾病的力量和勇气。
反观我自己:人生 41 载,我又获得了什么呢?
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我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出身五六线城市,只能靠勤学苦读走出小地方、走向大城市,改变人生命运。但对我来说,“苦”的不是读书,苦仿佛是我人生的底色,我常形容自己是“苦大仇深”,坚信“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这也是父亲从小灌输给我们的理念。
父亲是个军人,农村家庭出身,兄弟姐妹七人,他是老大。家里最饿的时候连活老鼠都吃过。后来他成为一名军人,也成了大家庭的顶梁柱。退伍后他转业到商丘市财政局。在我们家,他把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军人作风发扬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和哥哥极其严格,每次吃饭基本都是给我们上思想课,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拼搏。
从小我就知道我家条件不好。我们住在一个部队大院,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家都住着带暖气的楼房,而我家是平房,没有暖气不说,屋里还四面漏风,到了冬天室内都能结冰,手脚冻得红肿溃烂。壁虎、虫子在墙壁窟窿里爬来爬去。我和哥哥没什么玩具,玩的都是别的孩子扔掉的,穿的也是打补丁的衣服。在这种条件下,要想过上好的生活,就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而我们也不聪明,只能笨鸟先飞,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所以从五年级开始,我每天四五点起床,跑步、打拳、背英语。上了省重点中学,我经常是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考试大部分功课都是 100 分,同学们都管我叫“外星人”。但其实大家并不知道,我经常强制自己用一半的考试时间就提前交卷,多数科目依然可以拿到满分,以此严苛要求自己。
高考后,父亲在我的志愿表上填报了中央财经大学。他自己做财务,所以认为我学财务也理所应当,但我极度抗拒。我的目标是北京大学,而且要上我最喜爱的空间物理学专业,因为我一直的梦想就是当科学家,探索宇宙,探索 UFO(不明飞行物)。
不过家里的现实条件没给我反抗的机会。父母都是穷人出身,在他们眼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项能够傍身的技能养活自己,不是很好吗?
最终我还是服从了他们的意愿,科学家梦想破灭,还因此抑郁了三年。现实也容不得我继续抑郁,大三那年,年仅 47 岁的父亲去世,不仅让家里失去了顶梁柱,而且为了治病我们几乎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为此,赶紧毕业挣钱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
儿时家庭生活的窘迫和时常面对的困难,铺就了我人生的底色。大学毕业后,我进到机关单位工作,当公务员,后来又以全国统考系内前三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的公费研究生,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主任郝如玉教授。研二时,我被借用到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税改处,参与了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当时我国实施《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法》双轨制)提案等工作。研究生毕业那年,我参加了国家部委公务员考试,考了 150 多分,超出录取线几十分,但最终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进入当时世界 500 强排名前十位的三星集团,在中国总部担任税务经理,由此开启了我职业经理人的生涯。在那里,我接受的理念是“员工不加班,公司必然死亡”,员工就要为公司拼搏、拼搏、再拼搏。29 岁,我又加入万科任集团总税务师,那时候半夜离开办公室是常态,周末、晚上都用来研究房地产行业。
2011 年年底,我加入京东,有幸参与支持京东上市相关工作。2013 年 6 月,我带领团队开出了中国内地第一张电子发票,每年可为公司节省上亿元的财务成本,并将电子发票成功推广到各行各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几乎都是利用夜晚和周末的时间连续创业,为公司开拓新的价值。
我发过一条朋友圈:“没有谁强迫我加班,但我晚上总是工作到很晚,被人说是工作狂,可是我真的很有热情,尤其是面对棘手复杂的问题,事情越棘手、越难搞、越有挑战,我就越充满激情,越觉得又是我发挥能力的好机会,工作干得越爽。”
时间都投入在工作上,生活自然是枯燥的。我就是一个枯燥的人。在 40 多年的人生中,我几乎没有专门外出旅游过,别说是出国旅游,连国内游都几乎没有。仅有的两次出国,一次是 2013 年,为了拓展京东的国际化业务,去了俄罗斯;一次是 2015 年京东组织高管去美国硅谷考察。仅有的一次国内游是跟夫人去拍婚纱照。在北京上学和工作 20 多年来,我连故宫和长城都没有参观过。每年的年假也基本都是正常工作,连婚假都没休。
我几乎是在用别人双倍的速度回答着人生这份考卷,正如十几岁的我偷偷做的那样,总试图用一半的考试时间就交卷,且仍要求自己拿满分。老天爷大概也掐着表,在我人生半程刚过就提前过来,想要把卷子收走。然而这一次我还没答完,也不愿意离开考场。
我还能做点什么
这两年很多媒体采访我,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会得这个病,之前 40 年还会选择一心扑在工作上吗?”
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部工作机器,一个不能接受哪怕一分钟不工作的“奇葩”。我也知道他们大概已经预设了答案,那就是“不会,我会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享受生活”。这可能也是大多数绝症患者的选择。
但我的真实想法是:我仍然会像以前那样做。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这个世界第一绝症横在我面前,把毫无防备的我推下深渊时,很大程度上正是那种已经成为惯性的要强和拼搏劲头拽住了绳子的那一头,把我从深渊中一点点拉了上来。住院期间,除了刘强东刘总等个别领导和我的少数下属,公司上下都不知道我得病,因为我依旧参加各层级的会议,按时提交高管周报,手上的项目一个不落地向前推进。在一天天充满煎熬的检查和等待中,与其说工作需要我,不如说我更需要工作。
当然,绳子那头拉住我的还有更多的东西。
一天晚上 11 点半,早过了病房的熄灯时间,我还在查资料、处理工作,一扭头发现老朱还没睡。平时这个点他早该休息了。
“你咋还不睡?”我问他。
“等你呢。”
我突然想到,之前闲聊时他问我怕打呼噜吗,我随口说:“肯定怕,但是我先睡着的话你随便打,多响我都不会醒来。”无意间的一句话,老朱竟然记到了心里,每天都是等我先躺下,他再睡。
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能多活几年?
住院之前,我接触的基本都是商业精英或者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而这一个月来我结识了好多天南海北的病友,有些甚至不识字。以前我从未想到会和他们产生交集。他们都这么善良,本该拥有幸福的人生。
我想帮助他们。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强者,甚至成为王者,一次次努力超越别人,这也是社会的主流追求。但静下心来想,其实我们已经很强了,强大到具备了帮助别人的能力。相比于这些病友,起码现在我的身体状况要强不少,我还能正常行动,还有两三年时间可以支配。而且坦诚地说,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我也更有优势。
这大概就是上天要交给我的使命,它仿佛在说:蔡磊,这个病很残酷,所有病人都无比绝望,你还有点儿能力,愿不愿意为这个病的救治做点什么?
毫无疑问,我愿意。
我不是没想过趁有限的时间去旅游、享受生活,但我心里知道,那不是我,也不是我想要的。我的病友要么已行动不便,要么只能卧床维持,但是我还能战斗,那我就该去战斗。如果我们
自己都不努力,还能奢望别人为我们努力吗?
从敏捷战略到高效执行
OKR目标管理法 实践落地工作坊
关键词:
-
观察:通用技术中国医药三款产品中标第八批全国集采
资讯 23-03-31
-
火炬之光2存档位置在哪?火炬之光2共享仓库怎么用?
娱乐 23-03-31
-
大理寺发展都经历了哪些阶段?大理寺的官职设立和职责是什么?
社会 23-03-31
-
全球微动态丨徽州区:用好用足税收优惠 激活徽州高质量发展“一池春水”
资讯 23-03-31
-
帝王权术是什么?帝王权术的特征是什么?
教育 23-03-31
-
止损线如何设置? 止损线一般为多少合适?
资讯 23-03-31
-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分别是什么意思?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有什么区别?
金融 23-03-31
-
罗伯逊:仍相信我们能在各项赛事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得进前四-世界热资讯
资讯 23-03-31
-
星际争霸2配置有什么要求?星际争霸2是个什么游戏?
服务器 23-03-31
-
什么是安防监控?安防工程包括哪些项目?
安全 23-03-31
-
双系统如何引导修复?双系统引导修复工具详细操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服务器 23-03-31
-
三国塔防魏传怎么修改?三国塔防魏传为什么下架?
智能 23-03-31
-
三星r428笔记本参数是多少?三星r428快捷键驱动安装方法及常见问题有哪些?
智能 23-03-31
-
4月用户侧电价分析:超6成区域峰谷价差同比增长 新视野
资讯 23-03-31
-
dota巨牙海民如何出装?dota中哪个职业克制恶魔巫师?
大数据 23-03-31
-
魔兽世界猎人稀有宠物都有哪些?魔兽世界猎人天赋怎么点?
互联 23-03-31
-
从“高考状元”到贪腐两千多万被查:四川简阳原市长易恩弟忏悔书披露 环球微资讯
资讯 23-03-31
-
省消保委提起全国首例医美领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天天快看点
资讯 23-03-31
-
即时:送老舅的生日礼物
资讯 23-03-31
-
王博:诸暨对CBA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由衷地感谢你们 环球新动态
资讯 23-03-31

阅读排行
- 一个 45 岁的男人决定“打光最后一颗子弹”_天天亮点
- 【天天速看料】和讯个股快报:2023年03月31日 豆神教育(300010)该股换手率大于8%
- BM11-C3-200KG-3B (BM11传感器) ZEMIC 中航电测称重传感器 天天微资讯
- 网络设备有哪些?网络设备分为哪几种类型?
- 天衣无缝剧情人物解析_天衣无缝剧情
- 铁矿石价格异动不可掉以轻心
- 广晟有色:2022年净利2.32亿元 同比增67.03% 世界热头条
- 珠光控股(01176.HK)发布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业绩,该集团取得收入28.39亿港元,同比下降4.9%
- 国内首台超大直径TBM/泥水双模式隧道掘进机“华隧奋进号”正式下线
- 启动改造!涉及六安城区11个小区!
- 环球讯息:布依族图腾
- 蒜蓉炒油菜的做法_蒜蓉小油菜
- 贵阳五中怎么样_贵阳五中 环球速读
- 三星schi509怎么强制恢复出厂设置_三星sch i509
- 荣耀平板5玩和平精英(荣耀平板5怎么样) 世界新动态
- 姚曼:我是蒋大为情人,他欠我90万,有欠条为证,蒋大为:都是她逼我的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_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
- 就在今天,威少成为历史第一:在5支球队砍下至少30分10助攻!-焦点报道
- 今日讯!柯林斯宇航再获中国商飞年度优秀供应商两项大奖
- 每日消息!走吧,去济宁 | 刀枪剑戟 锋芒毕现
精彩推送
- 迅雷云盘在哪打开?迅雷X怎么设置下
- 好柿花生app挑战金可以退款吗?好柿
- mate50pro怎么开省电?mate50pro怎
- iphone14支持5g网络吗?iPhone14系
- 原神劫波莲位置采集路线分享?原神
- redmipad省电模式在哪里开?redmipa
- 右键菜单上传到迅雷云盘选项怎么删
- 网易有道词典怎么设置年级信息?网
- vivo即将发布操作系统OriginOS3 新
- 163邮箱怎么登录?163邮箱怎么撤回邮件?
- crm系统怎么改密码?crm系统数据如
- 密室逃脱6圆盘怎么转?密室逃脱6如
- 语玩怎么将我的动态设置为隐私动态?
- 黑盒工坊版本更新日志如何查看?黑
- 小影app怎么取消自动续费?小影怎么
- 安卓优化大师怎么卸载?安卓优化大
- 夸克浏览器神秘入口关键词大全?夸
- 掌上新华app保单贷款怎么办理?掌上
- 潇湘高考怎么看录取状态?潇湘高考
- 怎样看神马影院?神马影院播放时资源